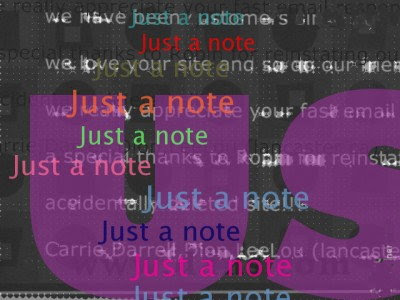The Passenger (1975)
The Passenger (1975)
原名:Professione: reporter (1975)
港譯:過客
Director: Michelangelo Antonioni
Screenplay: Michelangelo Antonioni,Mark Peploe
Cast: Jack Nicholson,Charles Mulvehill,Maria Schneider,Jenny Runacre,Ian Hendry
劇:
電視時事報導員 David Locke (Jack Nicholson飾) 到北非採訪關於遊擊隊的消息,無功而還,在返回居住賓館後,發現住在隔壁,之前在飛機上認識的 David Robertson (Charles Mulvehill 飾)突然死去,由於雙方面貌頗為相似,David Locke 突然靈機一觸,將護照上的照片互換,變換身份為 David Robertson,並聲稱自己原本身份 David Locke 已死,之後還按照 David Robertson 遺留下來的機票、行程表,到不同地方去,在途中,跟一名聲稱修讀建築糸的女子(Maria Schneider 飾)搭上關係,與此同時,David Locke 的妻子 Rachel Locke (Jenny Runacre飾),所屬電視台的監製 Martin Knight (Ian Hendry 飾)都希望跟 David Robertson 取得聯繫,採訪關於 David Locke 死亡之前的資料…….
評:
乍看之下,故事好像很沒有說服力,主角 David Locke 明明是個薄有名氣的時事記者,事業發展得不錯,連對方是什麼身份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情況下,怎麼會輕易對換身份? 其實導演在跟觀眾玩捉迷藏遊戲,將答案散佈在影片各處,要觀眾自己細心去找,然後加以整理。這也是 Antonioni 的電影特色,要求觀眾自己去尋找影片的內涵,而不是影片把細節内容一清二楚地說給觀眾聽,有別於現今很多電影的主觀旁述,Antonioni 在本片利用過往新聞片段以及訪問,來交待人物的過去,觀看時若不留心,就容易將其與現在進行的故事混淆。 從電視台監製的口中,可以得知主角 David Locke 是個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人,與別不同的成長背景令他能以不同的角度,客觀地看事物,這些令他成為出色的時事記者,然而在影片不時加插代表過去的片段裡,他敏銳的觀察力也是令他灰心消極的原因,因為他知道他採訪所得的大都是謊言,不真誠的言論,可是又不得揭穿人家,此外影片還反映了他妻子有婚外情,婚姻生活不愉快,這些都令他悶悶不樂,也造成了他想變換身份,過另一種新生活的動力。
影片結尾長達六分鐘半的長鏡頭,有一些觀眾認為只是展示拍攝技術,並沒其他用意,但其實這個長鏡頭用得非常妙,這個長鏡頭交待了片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情節,首先是 David Locke 在這個長鏡頭中死去,細心留意一下的話,就會發現長鏡頭開始時,David Locke 還躺在床上,悠閑地吸著煙,到了長鏡頭快結束,卻發現他已死在床上,換言之,David Locke 就是在這個長鏡頭中死去的,而他怎麼死的,卻發生在鏡頭畫面之外,交代得很隠晦,只聽見房内有幾聲聲響,很可能就是被那個進來的黑人用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幹掉的,原因就是 David Locke 所喬裝的軍火武器販子,支持武裝遊擊份子,因此成為當地掌權政府眼中釘, (在他第一次售賣武器予遊擊份子時,對方就已勸其要警惕政府特工),於是派特工把他幹掉。 (長鏡頭中出現的一黑人一白人是政府特工,這對黑白拍檔在影片中段,掌權政府派人緝拿購買武器的遊擊份子時,以及在以後跟踪 David Locke 的妻子時,都曾短暫出現過。)
其次是那個一直跟隨的女子,原來是政府特工,從她在房外目睹 David Locke 在房内遇害而不作聲,之後又跟那黑白拍檔中的白人煞有其事交談便可看出,這也解釋了為何之前 David Locke 曾在英國碰見她,到了西班牙又再碰見她,更多次出現在 David Locke 眼前,連 David Locke 也不得不問: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re with me?” 此外 David Locke 在一次交易中,等到肚子餓了也不見對方出現,該女子也一臉認真地慫恿其要等至對方出現,不要放棄。
第三是再一次證明妻子是個枭情寡義之人,長鏡頭的末尾,便衣警察指著她丈夫 David Locke 的屍體,問她: “Do you recognize him?”
妻子答: “I never knew him.”
電影裡第一次出現他的妻子時,她看著關於丈夫死訊的訪問,若無其事地吃著東西,喝著酒,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她聯絡 David Robertson,試圖探聽丈夫未死之前的情況,好像對丈夫還存在一點關懷,可是長鏡頭結尾這一句“I never knew him”卻證明了她尋找丈夫線索,很可能出於功利心,看看從中可得到什麼好處。雖然在大使館領取丈夫遺物時,發現丈夫護照上的照片已被更換過,並非丈夫本人,那時她開始懷疑丈夫是否真的已死,但是長鏡頭結尾這一句“I never knew him”,已反映了她繼續追查下去,並非出於關懷,而是為了查明丈夫之死是否屬實,會否影響她跟情人苟合。
單單一句“I never knew him”就把妻子虛偽做作、貪新忘舊的醜陋嘴臉展現出來,同時也反映了她追查丈夫之死的真正目的為何,對白精簡而又意味深長。
總括來說,這個六分鐘半的長鏡頭交代了,David Locke 要為自己變換身份的決擇負上什麼後果,同時反映了在他身邊的其實都是些不懷好意的人。這個長鏡頭是非常悲涼的,跟 Antonioni 一貫所表達的疏離,生存的痛感,一脈相承。
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長鏡頭,開始於 David Locke 在床上吸煙,然後鏡頭朝室外緩慢移進約兩分鐘,同時看著室外人物的活動,到了出現黑白特工,開始定鏡片刻,直到黑人特工進入室内,出現幾聲類似無聲手槍聲響,白人特工在室外探頭張望室内情況後,鏡頭又開始慢慢朝室外移進,此時在室外的只有那名一直伴隨在 David Locke 身邊的女子,跟白人特工交頭接耳,然後又閑步走動著,直至出現警車聲響,鏡頭已完全移出分隔室内室外的鐵欄杆,隨著警車出現,鏡頭向左移,然後再隨著那名女子向右移,此時又一輛警車出現,David Locke 的妻子與便衣警察前來,那名女子與 David Locke 的妻子和便衣警察一同進入室内,鏡頭也跟著從室外拍攝室内認人情景。整個長鏡頭就是先從室内慢慢移進,越過鐵欄杆,移至室外,然後跟著人物的移動,再反過來拍攝室内情況。這個長鏡頭出來的效果挺不錯,與其說展現了卓越的拍攝技術,不如說體現了 Antonioni 優秀的場面調度技巧,長鏡頭裡涉及許多人物,如何安排各人在合適時候出現,讓他們協調得當,不許早,不許慢,這無疑更考功夫。此外 Antonioni 這樣安排 David Locke 在鏡頭畫面之外被靜悄悄殺死,比起之前傳統在畫面上明刀明槍殺人,來得更有新意,不落俗套。
令人留下較深印象的還有影片中段的那個平移鏡頭,追踪來來往往的車輛,有點像 Jean-Luc Godard 的 My Life to Live (1962) 裡面,Anna Karina 偷拿鑰匙,被守門人捉住,然後押回去的那一幕,兩者的鏡頭都隨著快速運動的事物移來移去。
Antonioni 透過 David Locke 的故事,探索了生命與身份的問題,是否活得不如意,就須放棄生命,尋求別的新生命,又或者當對自己的身份覺得不稱心,就必須換上別的身份,前提當然是有機會可供選擇,就像主角 David Locke 那樣,然而就算有新生命,又或換上新身份,是否就一定比原來的更好? Antonioni 透過故事跟我們說並非這樣,David Locke 那樣偷用他人身份,去掉本身身份,其實是在逃避自己,而非改造自己,在獲得了新的自由的同時,也陷入了孤立無援的陌生處境之中,即使變換身份,飄洋過海,最終仍然是悲劇收場。
David Locke 的舉動起因於在發達的現代文明背後,人卻存在精神上的危機,感情上的隔閡,人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容易有自我輕視,生不如死的念頭,因此才有抛棄自身生命的衝動。但假若可以選擇其他的生命也未必是好事,如果生命有多次,那麼人就不會珍惜之前的生命,一遇到困境不順心就想放棄現有生命,盼望下一次的所謂“新生命”,這樣便造成更多被浪費了的生命,因此,一次的生命最好,因為一次就是全部,就是永恒,人才會勇敢去面對該生命中的苦與酸,在苦與酸中成長,壯大自己的靈魂。David Locke 的故事告訴我們,就算真的有機會成為別人,也未必就稱心如意,說不定別人的生命比自己的壓力更大,更危險,到頭來還是老老實實做自己最好,勇敢去面對自己的問題,總比逃避更好,至少有點敢做敢當的氣概。
David Locke 最後在房間裡很隠晦地死去,跟片首被他交換身份的人因心臟病發猝死相呼應,短短六分多鐘,便從活生生,在床上悠閑地吸著煙,到一動也不動,Antonioni 借此說明人生的無常,日子的苦短,如白駒過隙,這種情懷從消極面來看,是感歎時間飛逝,人生短暫; 但是從積極面來說,則是勸勉觀眾要把握時間,不要讓有限的時光白白浪費掉。Antonioni 的情懷屬前者居多。
從加插進去的過去片段來看,David Locke 所採訪的對象都不願講真話,所說的都經過過濾,這又反映了 Antonioni 對新聞可靠性的懷疑,提醒觀眾對新聞要保持清醒的態度,不可盡信,這未必是新聞工作者的問題,而是提供消息的一方,對消息作了若干篩選、修飾,這樣消息到達讀者腦裡,已非原來面目,同時也滲進了消息提供者的立場,喪失客觀性。
影片中段 David Locke 跟一老者的對話,老者指著一群正在玩耍小孩說:“I’ve seen so many of them grow up,Other people look at the children,and they all imagine a new world. But me….when I watch them,I just see the same old tragedy begin all over again. They can’t get away from us.” 表面上這番話在說小孩,但事實上已經預示了男主角最終的命運,也是對世人未來的悲觀,再細心一想,不幸固然跟外界有關係,但本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David Locke 不安守本份,偷用他人身份,以及財產,這已經是偷盜、貪圖他人所有。其次,David Locke 第一宗軍火交易就在教堂裡,耶穌主張人要仁愛、和平,卻在教堂裡進行軍火交易,明目張膽在天主面前犯了殺誡,這是存在主義、道德淪喪的表現,那麼他種種不幸,甚至最後客死異鄉,也就有了點咎由自取的意味。Antonioni 對人的前景是悲觀的,可是這悲觀之中,Antonioni 又認為部分原因是人本身所造成。正如他的前作 The Red Desert (1964) 中的高頻噪音, 工厰區煙囱噴出黃煙,既然人本身就在污染環境,也就不要埋怨大自然的報復。
Antonioni喜歡在影片中採用大量自然真實聲響,少用配樂,例如 L' Avventura (1960)中的波濤激浪聲、強風呼嘯聲、快艇馬達聲; La Notte (1961) 中的飛機穿過聲、救護車鳴叫聲、暴雨敲打聲; Eclipse (1962)中的水渠流水聲、植物灌溉器噴洒聲、車輪輾磨聲; Blowup (1966)中的相機拍照聲、樹梢搖拽聲、雀鳥鳴叫聲; 本片也一樣,全片大部分時間都沒有配樂,純粹周圍環境的聲音,或者雜音,而這些雜音,也正是主角荒涼無定向、飄泊無根的内心寫照。
本片在拍攝完畢後,Antonioni 剪出了一個長達四小時的版本,之後又經其他剪接師剪短成二個半小時,可是電影公司 MGM 對此仍不接受,要求片長不能超過二小時,以便在北美巿場發行,於是便出現了 119 分鐘版本,David Locke 返回英國倫敦家裡一幕就在這個版本中被剪掉,1983年,Jack Nicholson 跟電影公司商談,意慾購買本片的底片,最終在 1986 年成功購得本片所有版本的版權,到了九十年代,一些國家購買將本片製作成錄像帶出版的牌照,日本的牌照期限較長,長至出現 DVD 技術之後才期滿,以致之前唯一出現本片的 DVD 版本,只有日本一家,不過日本的版本製作得不好,畫面偏黃,Jack Nicholson 對於劇院版和日本版 DVD 都不滿意,逐於 2004 年 5 月和 Sony Pictures Classics 達成出版 DVD 的協議,而新出版的 DVD,據稱是來自保存得較好的底片,影像色彩較為平滑自然,光暗對比度更加清晰分明。
My Rating: 8/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
Thursday, May 18, 2006
The Passenger 過客
Posted by
Tourist
at
7:40 PM
![]()
Labels: 2006, Movie Reviews